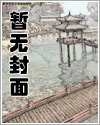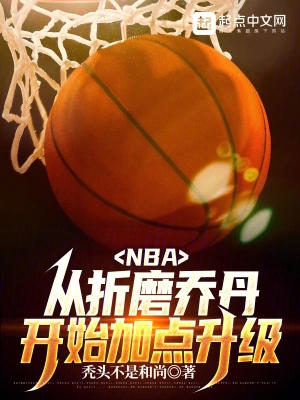第12节
李司仓:“想学道!”
导师:“学道?”
李司仓:“是啊,王老介绍我来的。”
导师:“你还是回去吧。”
李司仓:“为什么?”
导师:“我看你的面相,有官禄之命。等你官禄之命到头了,再来不迟。”
王老一耸肩膀,表示没办法。
李司仓:“可是……”
王老:“对了,山下有人要两头牛,就是你我来时遇见的那个山民,你顺便把牛带给他。”
李司仓:“我去哪儿搞牛?”
王老:“这里有卖的。”
李司仓:“牛……”
李司仓真的就买到了两头牛,也许是王老出的钱,总之他带着两头牛又攀藤附树,按原路爬了下去。至于那牛是怎么爬的,我们不太清楚。来到山脚下后,按王老吩咐,李司仓把牛送给了山民。当他再回头时,发现身后通往仙境的山路以及那藤树都消失不见了。
回过头来,继续说契虚的故事。
从稚川回来后,契虚继续归隐太白山,唐德宗贞元年间,转移到华山修行。
在唐朝,华山、终南山和太白山,为关中地区道家三大隐居地。在华山,和契虚一起隐居的还有一个叫司马郊的人,此人是个自然主义者,视山川为帷幄,以禽兽为伴侣,每日食山鸟衔来的野果。
在华山,契虚一隐就是很多年。
在古代,“仕”“隐”“仙”三个词是始终纠结在士人的内心的。在这里,不妨说说古时的隐逸风尚。在这种纠结中,“隐”处于中心位置,所谓低头寻仕途,抬头望仙云。
隐逸理想,在中国古代的士文化中太重要了。归隐泉林,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“天子不能臣,诸侯不能友”,这是古代隐士秉持的坚定信念。
印象中,隐逸是道家所独有的。但实际上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大树上,同样有着隐逸的叶片:“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”不过,这里说的隐,仍是在以“入世为本位”提出来的,或者说是被动的,而并非像老庄道家尤其是庄子之说,完全出自对个人终极价值的追求。这是儒家和道家关于隐逸理想的最根本的区别。明白了这一点,就好理解中国古代那些有关隐逸的人物、文化和历史了。
那么,到底该如果定义隐士?
隐士当然不是隐居不仕的人,而是隐居不仕的士。一字之差,谬之千里。否则的话,游走山野的樵夫也算隐士了。澳大利亚汉学家文青云对于隐士有个说法:“对于任何隐逸而言,关键的要素是自由选择:不管一个隐士出于什么理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 第4页 / 共13页
相关小说
- 美人疯批们的甜腥鲍鱼汁
- 短片 美人,双
- 628500字10-25
- 轮回乐园
- 21843343字12-25
- 温宁厉北琛
- 他的嗓音听起来优雅低沉,十分强硬。她狠狠地瞪着他,那晚的禽兽力大无穷,而眼前...
- 2541829字05-31
- 中国足球百年风雨历程
- 《中国足球百年风雨历程》小说是作者桃松子写的一本情节俱佳精品小说,中国足球百年...
- 929689字08-09
- NBA:从折磨乔丹开始加点升级
- 8417687字04-06
- 总是场恶梦「嘲笑」
- 在班上受到排挤的娜允 受到了心魔安媚的的帮助 安媚想要做什么呢? 还是...
- 17459字08-1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