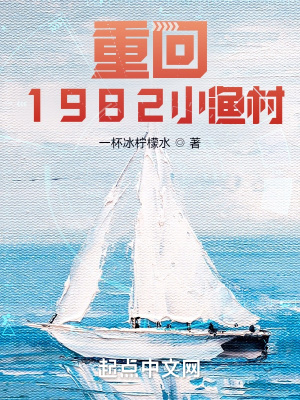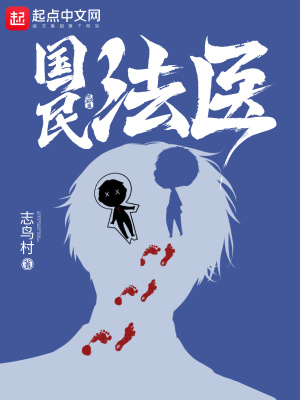第11节
人便是这样,总要有人替你出头才显得矜贵,自己顶回去,再伶牙俐齿,都显得寒酸。方晴这样“矜贵”的机会不多,一样的妯娌姑嫂,总不好太偏帮谁。
方晴自己虽也算得口齿伶俐,却顶不会吵架,一生气就蒙头,刚嫁过去那阵子很受了几句话的闲气,但日子长了,脸皮厚了,棱角磨得圆乎乎的,竟然跟这一大家子处得融洽甚至亲香起来——方晴叹口气,冯家说到底都不是坏人。
了不得,再这样下去,连三岁打破个碗的事都得寻思一遍,方晴深感自己得找点儿事做。
又兼盘算银钱,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了两个匣子,一个里面放着绞丝银镯子一副、镶红玛瑙金镯子一副、素面金戒指两个、金镶红宝耳坠子一副、石榴花头小金钗一对、银鎏金嵌宝项圈一个——有新打的,但多半是祖母和母亲的陪嫁;另一个里面是100块大洋。
这匣子方晴当然都随身带过来了,其中头面多是祖传之物,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动的,其实单100块大洋也不是个小数目,但也架不住坐吃山空。
这天津卫不比乡下,东西都贵得离谱,米面菜样样要钱,饶是方晴单身一人吃喝,每个月也要三四块,一年就是三四十,还有房租呢,更别说冬天点炭炉子买厚被褥……至于冯璋能给多少家用,方晴不知道,也不敢完全指望他。
难道真去卖画儿?方晴想起琉璃厂被礼送出去的卖画人,对自己这两下子不自信起来,还是找点别的活儿干吧。一个姑娘家,能干什么呢?
没辙又无聊的方晴便跟钱二嫂和刘大娘一起纺线、打褙子。
方晴这纺线的技术还是在冯家时练的。树荫下,蝉鸣里,一长一短的抻着,很快小半天就过去了——方晴喜欢这种单调、轻松、不用脑子的活计。
但方晴还是更喜欢打褙子。
褙子是用来做鞋底的,一层布铺在板子上,抹上糨子,零碎破布再拼一层,再抹糨子,再拼一层,如是三四层,晾干,即为一张。和纺的线一样,这褙子也是有专人上门收,都赚不仨瓜俩枣的钱,妇女们闲着也是闲着,换两斤棒子面也好。
打褙子的时候,方晴兴趣上来就按颜色贴,柳绿配鹅黄,松花配桃红之类,偶尔还能拼出个图案,方晴觉得跟某些西洋画类似——在琉璃厂淘的那本《西洋画概览》上有这么一类,呼之曰抽象画。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 第1页 / 共7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