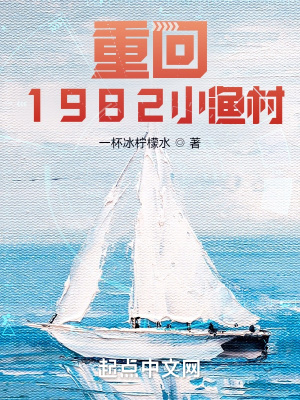第60节
“记者厉害啊。当时还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要知道,潘越家也不是无根基的,在公安系统内也颇有一些关系,他们通过渠道,找到了局里的人,知道了我们调查进展,发现我们郗羽有点怀疑,又弄到了郗家的地址。潘越的母亲冲到郗羽家里去里大吵大闹,要郗羽偿命。郗羽的母亲是日报的记者,还是比较出名的那种,人脉关系很广,她愤怒地找上分局,要我们对泄露信息负责——更重要的是,她还联系了许多外省的媒体要曝光我们,说真的,局里当时非常被动。”
李泽文听到此处,也已经明白了,这段小插曲才是徐云江对这件案子印象深刻的导火索。
“第三个原因,也是最重要的原因,案件没有线索。我们没有找到目击证人,潘越的情绪不好是事实,日记里的悲观情绪也是真的,死亡的特征也完全符合自杀的特征——法医实在找不出他杀的证据。我们内部倾向认为,潘越和郗羽放学后见了一面,两人或有争执,甚至发生了肢体接触,然后她离开,潘越想不开坠楼。”
“没有人怀疑是她推人下楼的?”
“个别人有这样的想法,大部分人不认为如此。第一,她是女生,虽然长得高,但是非常纤细,潘越的个头虽然矮小一点但是男生,看手腕的粗细也知道他的力气比郗羽大多了。第二,郗羽这个女孩子……”徐云江的表情凝重起来,“不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完全不像能干坏事的人。”
李泽文知道他的意思。早年的犯罪学里有一种对罪犯相貌的研究,这些研究者试图总结出重刑犯们的长相的规律,从他们的外表,比如脸部的轮廓、耳朵的形状、头发的颜色判断他们是否可能犯罪——这种理论类似我国古代的“面相学”,很快被斥责为“奇谈怪论”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。但不论怎么说,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总会对其他人的长相做一个下意识的判断。而郗羽的的确确长了一张“最不可能犯罪”的脸。
要怀疑一个品学兼优、人人夸赞,眼神清澈且笑起来有一对美丽酒窝的女生犯下了谋杀罪,也相当挑战人的三观——警察们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。
李泽文说:“但无论一个人的长相如何,都不能凭面貌洗脱嫌疑。”
徐云江说:“当然不能以貌取人。但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,我们就会倾向相信面貌。退一万步说,就算是她把潘越从楼上推下去又能怎么办?她不满14岁,就算是杀人放火也不用负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 第7页 / 共8页
相关小说
- 重回1982小渔村
- 重回1982小渔村最新章节由网友米饭的米免费阅读提供,《重回1982小渔村》情节跌宕...
- 4196390字06-05
- 八十年代渔猎日常
- 78454字09-23
- 和闺蜜男朋友合租之后
- 和闺蜜男朋友意外合租。 关键是!!! 半个月前方瑶在闺蜜家借住,差点被她...
- 113247字10-01
- 美好生活从相亲开始
- 1111452字01-02
- 吞噬星空2起源大陆
- 《吞噬星空2起源大陆》小说是作者我吃西红柿写的一本情节俱佳精品小说,吞噬星空2起...
- 1070030字02-04
- 追尾
- " 李杨骁是个落魄的小演员,因为一起连环追尾事故,遇到了京城高干迟明尧,两个人...
- 253071字04-2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