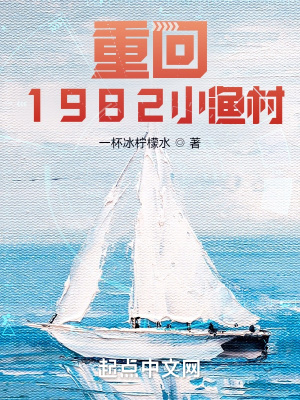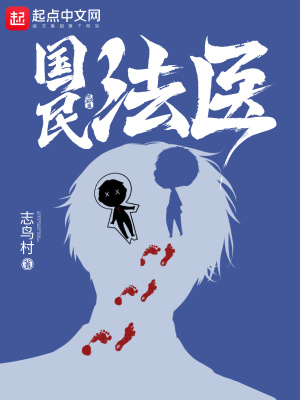欺人太甚
尝试分析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的关系。首先,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年龄相仿,“太平公主者,高宗少女也。以则天所生,特承恩宠。初,永隆年降驸马薛绍。”设若永隆年(681年)降驸马薛绍时年十六,则太平公主应生于麟德二年(665年)前后,正与生于麟德元年(664年)上官昭容年龄相仿。其次,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同在宫中长大,具备频繁接触的条件。再次,上官昭容曾与武氏过从甚密,而太平公主的第二任驸马武攸暨正是武氏家族成员。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有私交和相同政见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结合《墓志》“词旨绸缪”的描述,不难想象,上官昭容的安葬,太平公主有游说睿宗的莫大之功。而实际上上官昭容葬礼的资助者正是当时踌躇满志的太平公主。
唐代有碑志之序、铭分别请人撰写的先例。《上官昭容氏碑铭》篇题注“齐公叙不录”,铭文亦提到“或穆齐公,叙其明德”,可见该碑序文由齐国公崔日用所撰。仇鹿鸣在《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》一文中认为“崔日用在唐隆政变中立下大功,因获封齐国公,其于景云元年七月入相,但仅月余便因与薛稷不合而遭罢相,寻出为扬州长史,历婺、汴二州刺史,兖州都督,荆州长史。因而景云二年七月,崔日用并不在长安,自不可能为上官婉儿神道碑作序。”“神道碑与墓志应作于同时”其说甚是。然而我们认为,在景云至先天年间,对于上官昭容不存在“平反”的问题,实际情况是:唐睿宗在太平公主的游说下给了上官昭容肯定的评价,而唐玄宗即位后并不认可。
仇鹿鸣《上官婉儿墓志及其透露的史实》:后来李隆基因一时无法扳倒太平公主,不得不暂作退让,礼葬上官婉儿。墓志长七十三厘米,宽七十五厘米,是初唐三品官员墓志常见的规格,其最初可能还是按婕妤三品的身份来安排葬事的。从制度规定而言,赙赠与遣使吊祭皆当出自诏命,如《通典》规定诸职事官薨卒,文武一品赙物二百段,粟二百石,以下按品级递减。五百匹之巨,远远超过礼制。
仇鹿鸣《碑传与史传-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》:并于景云元年八月将其礼葬。但从志文的书写及葬事的安排中,仍可看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互相角力的痕迹。如前所述,志文中虽凸显上官婉儿忠于中宗、反对韦后的一面,但并未叙及其草遗诏引相王辅政之事,故上官婉儿虽是前朝忠臣,但无功于新帝,对其评价仍有所保留,进而限制了葬礼的规格。墓志通篇称其为婕妤,文中虽已记礼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 第6页 / 共7页
相关小说
- 和闺蜜男朋友合租之后
- 和闺蜜男朋友意外合租。 关键是!!! 半个月前方瑶在闺蜜家借住,差点被她...
- 113247字10-01
- 重回1982小渔村
- 重回1982小渔村最新章节由网友米饭的米免费阅读提供,《重回1982小渔村》情节跌宕...
- 4196390字06-05
- 八十年代渔猎日常
- 78454字09-23
- 老实人有四个男友(NPH)
- 大家好,我叫孟瑶祝,一个平平无奇、老实传统的读书人。读书读累了,就想找个男人...
- 46751字04-11
- 国民法医
- 尸体:请问你礼貌吗?
- 3971414字02-08
- 吞噬星空2起源大陆
- 《吞噬星空2起源大陆》小说是作者我吃西红柿写的一本情节俱佳精品小说,吞噬星空2起...
- 1088556字02-08